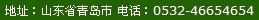|
长沙白癜风医院 https://m-mip.39.net/nk/mip_4693377.html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逢到从夏入秋的时光,那正是摊档调换的时候。风光了一夏天的棒冰摊子,你再也听不到木板敲击木箱子的“邦邦”声,也看不到那个中年男人堆满了格格巫般的笑容,伸手递给小女孩们一根根积满了色素香料的苹果棒冰橘子棒冰草莓棒冰的情形。略带仁厚之心的,推着小轮车,用棉被捂着清凉饮料水,卖五分钱一杯的阿姨,应该也回家织毛衣去了,她和棒冰阿叔的死磕要到下一个三伏天才会再度上演。 而换上的那一批摊档之间的生意较量,却有越来越火热之势。校门口东边是一位生得白净的阿婆,最喜穿青灰色两用衫,戴着小碎花袖套,每日坐在一个塑料小凳上,守着面前嗞嗞作响的小油锅,用四只长柄模子做油墩子。校门口西边则是一个佝偻着背,看上去有严重哀怨之相的满脸皱纹的阿婆,头发每每都梳不整齐,随随便便地用一只铁夹子挽着,没夹进去的几缕在秋风中萧瑟地飘扬着。她大多数时候都穿颜色暧昧的粗针毛衣,黑不黑,灰不灰,青不青,蓝不蓝,望着眼前那一锅颜色深重的茶叶蛋和豆腐干,阿婆会忽然惆怅地猛吸一口鼻涕,然后叹一口气。 两位阿婆犹如是在我们小学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各有一批死党小朋友做拥趸。有的喜欢油墩子阿婆说话和蔼,知书达理,用来炸油墩子的油干干净净,炸出的油墩子色泽金黄,里面包的萝卜丝香甜滚烫,还细心地拌了些小虾米。她常常一边炸油墩子,一边教小朋友些卫生常识,比如要洗过手才吃东西,如果没有地方洗,就可以带一瓶子酒精棉花先擦擦手,再吃之类。说着还真的拿出一个装满了小粒酒精棉花的带盖广口玻璃瓶,那些买了油墩子的小孩,在这里得到很好的卫生再教育,一个个都被震慑了,先擦手才敢去拿那油墩子,吃完之后再领一张油纸吸手上和嘴上的油。 另外一群小朋友,则是喜欢那位茶叶蛋阿婆的不拘小节。她没事从不跟小顾客唠叨,更不会说教,如果有人跟她说“要一只茶叶蛋,一块兰花豆腐干”,她便先用似乎经常迎风流泪的眼睛定样样看你几秒,然后心不在焉地从锅里捞出一蛋一干,放在看上去是跟食物完全不相干的裁成四方的白色复印纸上,“啪”地涂上一坨与其分量非常不相称的甜面酱。 但也许就是因为这多出几倍的面酱,却令她做的豆腐干分外美味。也因为那丝毫不吸油也不吸水的复印纸,你用它包着茶叶蛋一路吃,卤汁和酱料便一路往下滴,更造就了登峰造极的野食体验。大啖而饱的小学生们,经常在吃完后,把那仍然留着面酱的复印纸“扑”地贴到阿婆身后的墙上,而邋遢的茶叶蛋阿婆则是丝毫不在意,她只是在一堆生意成交后,又陷入了新的木然和迎风流泪中。 我尝过东宫阿婆的油墩子,也试过西宫阿婆的茶叶蛋和豆腐干,总体来说,我觉得那油墩子面粉塌得略厚了,恰似东宫阿婆的人格一般,外皮金光灿烂,内心也算丰富,但不知怎的,中间那一层总隔得有点厚,让人觉得有点疏远。 并且我不大喜欢她在讲解卫生小知识时刻意拔高声调,压扁嗓音的模样,仿佛是故意想让西宫那位听到一般。示意谁比谁高级的姿态,就连小孩都看得出,一到这种时候,大家都会默默地聚拢到一个方向,朝着西宫的方向无声地发笑。而西宫那边,大部分时间是没有反应的,除了机械化地重复涂酱和收钱这两个动作之外,阿婆的表情只有在吸鼻涕的时候,现出一丝鲜活。其他的任何一秒钟,她仿佛都是对外界的一切别样声音、影像,失去感应的人,她的半黑不灰,半灰不白的几缕乱发在风中纠结着,仿佛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与这个世界失去联系的,而这种时刻,我便会觉得,她仿佛穿着一件是用自己头发编结的粗针毛衣,而她所卖的茶叶蛋和豆腐干,也因为随着她一起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这才变成了人间难得的美味。你知道,有时候,如果你在你的食物里放入了你太多的灵魂,那食物也是会变味的。而西宫阿婆的茶叶蛋和豆腐干,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她干脆就放弃了要把它们煮好的这个愿望,这些食物在黑漆漆的锅里变得如此空洞,全无灵魂,但也因为如此,它们获得了一种奇诡的美。 我从小就爱思索关于食物的问题,不是因为别的,完全是因为胆怯,自卑。当所有孩子都想干大事,将来出人头地的时候,我已经深深了解到,自己完全不能胜任什么可以改变人类的大事。我的眼孔太小,每次只能看全一块蛋糕的长宽高而已,所以,我不如多想想关于食物的问题。但从食物说开去,又有两点,我是提前认识到的。那就是——1,虽然我琢磨食物,但这并不代表我要成为厨师。成为某种东西的创造者,那也真是够令人害怕的事情,无论造出什么来,其结果都令人毛骨悚然。所以,我还是光思考比较好。2,虽然我会在琢磨食物的过程中吃各种食物,但变成一个胖子,也是让我害怕的。节制是个很重要的环节,无论是爱食物,还是爱人,都必须有节制,以及不徐不急,也只有这样,你才比较容易接近某一种食物,或某一种人,的真相。 话说摊贩的争奇斗艳实在是一件值得细细咀嚼的事情。那一年的深秋,东宫西宫之间又来了个卖烘山芋的老者,一眼望去,他所携带的制作烘山芋的全套家什要比两位女性的装备看起来规模宏大得多。一只微微偏向深绿色的其实质却是黑不溜秋的斑驳铁皮大桶,以歪斜却看上去屹立不倒的扭曲姿态嵌在他三轮车后厢的一堆砖头里,桶的最上方覆盖着一块布满土尘,但却让人感觉保温功能极好的厚棉毯。老头的紫酱色面孔粗糙之极,充满了所有你可能想象到的老头所能经历的风霜,却又搭配着一双不和谐的狡黠小眼,证明着他始终不甘心于自己所操持的作为营生的那些活儿,当然,卖烘山芋也只不过是他人生匆匆而过的一方小堂会而已。 当天气冷到可以哈出白烟,烘山芋老头的生意已经好到了极点,他用粗砺得跟手套皮一般的手生生伸到棉毯底下,从大桶中掏出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看上去都跟那块旧棉毯极其类似的烘山芋,而那些被冻红耳朵的小孩便贪婪地捧着吃。事实证明,就算烘山芋的内里可以用金黄色来形容,它们的味道依然不能被百分百地确定为香甜。但无论什么样子的烘山芋,首先便用它们的气味造了谣,在寒冷的空气里散布着关于甜、糯、香的谬论,以至于那些买烘山芋来吃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吃而吃,他们只是为了寻找一种能够落实那气味的东西罢了。 但烘山芋老头显然对这样的气氛渲染仍不满意,有时候他会抽一根烟,绘声绘色地对这些站在小吃摊前的孩子们讲述他以前在农村时怎样宰掉一头羊的故事,以及如何烹饪那一整只羊。前半段悲壮又荒谬,后半段则是挑动人口水的华彩篇章。金红色的脆皮偶尔被人不小心碰碎一块,便发出咔嚓的小小爆裂声,细嫩的羊肉和与其紧密联系的脂肪层肥美多汁,乳白色的羊肉汤浓稠得搅不动,因为羊杂全切开放里面了,每一种都炖到酥烂。刚放学的饥饿的孩子们听着瞪大了眼睛,老头得意地用小眼珠偷瞄着东西两边那两位业已失宠的阿婆,她们都无例外地呆滞着,只是不时为自己的锅灶添一把火。 老头在那种时候的表情,简直像是同时拥有两位妃子的皇帝一般,而我幻想着他苍老的脑袋中的图画,也许也就不过是一间生着火的温暖的小屋,老头在中央,两位老太太一边一个地安静坐着,三个人围着的,是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羊肉汤。 同样是那一年,我在学校做了件不够接近真相的事情。校领导指定了两个四年级的女生去参加区的作文竞赛,我,和另一个眼镜女。学校老师们纷纷认为,我跟她代表了两种不同特色的作文竞赛选手,她博览群书,以真诚和热情书写各种同龄小学生仍不太明白的知识,很容易获得评委的嘉奖;而我的优势则是爱编造,爱想象,虽然有时候我写出的故事有点天马行空,但这毕竟是小学生的作文竞赛,也许评委会被“孩子纯真的想象力”所打动。这样的评论,在我看来很是不明真相,因为我心里觉得,我跟眼镜女并无区别,我们不过就是两个在这样的年龄混迹得成功的撒谎精罢了,只不过她热衷撒激情洋溢的关于社会责任感的大谎,而我喜欢撒点给生活润色的小谎。 正式比赛的前几天,眼镜女找我一起走路回家,我们先是假惺惺地沉默了半段路,接着我便忍不住地问她有什么准备写的吗。她答,一定会写珍·古道尔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把这个人编织进她的作文,同时也警告我不许打她这个选题的主意。“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她转而一想,又高兴地说,“反正你也不知道珍·古道尔是谁。” 但是她错了,我还真的晓得珍·古道尔是研究黑猩猩的女科学家,但我确实对黑猩猩不感兴趣,只是我在看珍·古道尔的传记时,有一段她观察黑猩猩吃一只野猪仔的描写,让我感到血腥又充满食欲。但接着看下去,珍·古道尔在猩猩群里吃的仍然是些野果,这令我大失所望。也许她应该大展人性,想吃肉时便伙同猩猩一起去打猎,并且最终教给猩猩们把生肉煮成熟食的方法,这样,那一群丛林中的猩猩便会自此开始一种新生活,说不定还能迅速进化成人类。是的,当时的我,便是这样无限怜悯地替猩猩们考虑的。 眼镜女算是撞到了好运,那一年我们拿到的作文题是《我崇拜的人》,她理所当然地边哼着小曲,边把她前几日费力背诵下来的珍·古道尔的对动物的爱心和对科学的投入全部写到了那一张密密麻麻的方格纸上。而我则是踌躇了十分钟左右,用铅笔在桌板上画了几个小动物之后,只能想到去追随眼镜女的脚步,也写一个动物学家。但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她,不跟她写同样的珍·古道尔,我便挑选了埃列克·齐门。事隔多年,我已经忘记了当年我喜欢的这位动物学家是法国人还是瑞典人,但我清楚记得他在狼群中的生活,和硕大的灰狼相互快乐地扑打、撕咬,四肢着地地走路,并且学着吃生肉。但是写着写着,我便忍不住地开始编造,想象着埃列克·齐门在狼群中也会有思乡之苦,而思乡则是有一大半是思恋食物。有一天,狼群打到一头羊,他便突发奇想,要给整个狼群烤羊肉吃。 他偷偷从其他地方搬来木柴,架起柴堆,一开始,狼群以为他想要背叛,独吞那只羊,但又迫于烟火气太重,只能围成一圈,在他烤羊的全程对着他嘶吼。写到这里,我开始大段地把烘山芋老头口中的烤羊过程搬上了方格纸,而埃列克·齐门那沧桑的欧洲面孔上,也长上了一对中国人狡黠的小眼珠,他一边神闲气定地烤着被开膛破肚的肥羊,一边环顾周围饥饿又无邪的狼群,羊油一滴滴落在烟熏火燎的柴堆上,他这是发誓要用食物彻底俘获它们的心。 方格纸显然不够我发挥如此长篇,有年轻女监考老师走过来清脆地说了句“可以写在反面”,陡然击碎了我的迷梦,于是我匆匆收尾,来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参赛用纸的背面赫然写着,最后埃列克·齐门成了狼王,他用人类的烤肉方法征服了整个狼群。而在他告老还乡之日,他的心愿也就是在乡间开一家小小的烧烤铺子,坐在里面啜饮几杯苹果酒,回忆他传奇的一生。 期末的时候,我被通知那篇作文获得了一等奖,而眼镜女只屈居二等奖。那些胡编乱造的情节竟然没有人看破,让我欢乐又惴惴不安了一晚上。几天后,校长去取了奖状回来,我那篇激动人心的烤肉文在学校的每个老师手中传阅,竟还是没有人发现最精彩的部分显然是不近情理的胡说。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为自己感到害臊,眼镜女也温柔地对我甘拜下风。小学生果然是很简单,她只恨自己没有早一点看到埃列克·齐门的传记,这样一比较,珍·古道尔吃得简直是太清淡,太无聊了。她友好地问我,能否把传记也借她一看,这让我立即慌了神,于是顺口又撒了一个谎:“你看不懂,那是法文的。”于是眼镜女悻悻走了,整件事便告一段落。 直至今日,有时候我还会想起烘山芋老头的烤羊肉故事,及其为我人生开辟的一方稚嫩的小天地。通常会在冬天的涮肉店内,无论是黄铜锅还是不锈钢锅,总之锅里都是翻滚的肉汤,众人嬉笑着,用筷子挟着薄薄的羊肉片一拥而上,此时我便在澡堂子般雾气氤氲的涮肉店某处,看到了埃列克·山芋绘声绘色地讲着关于宰羊和做羊的故事,身边则是一群天真无邪的狼。 哪怕做再简单食物的人也是厨师,哪怕是做再简单食物的厨师,也有表演欲和统治欲。他们热火朝天地为别人制作着各种味觉,自己却永远不会选择自己做的东西来充饥,因为怕一不小心就吃到了他们自己的迷思。所以我不想自己当厨师,因为我实在太珍重自己的饥饿感,以及如何去满足这种饥饿感。而厨师们,他们都是些阴谋家,他们必须忽略自己的饥饿感,才能为别人做出像样的食物,如果他们过分关心自己,那就永远成不了大事。某种程度上来说,厨师是没有欲望的,他们只有野心,而不存在欲望这回事;他们有出色的鉴别能力,但他们绝不会说:“唔,我想吃那个想很久了。” 元旦快乐呀今晚你们的跨年晚餐是什么?明年对自己,对家人,对悦食君都有什么希望呀?到留言里跟大家快乐地聊一聊。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gejiuzx.com/gjsxw/7602.html |
时间:2020/9/15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泪流满面这里的房价,比鹤岗个旧还l
- 下一篇文章: 新昌这两个旧小区将改造建设费用约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