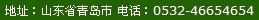|
作者分别在第一和第二部分讨论了美国与德国史学界中的兰克形象。在美国,兰克被尊为“科学派”历史学之父,“被认作是只注意于确认事实”的非哲学的历史学家;在德国,历史学家们则“深深知道兰克通过对于独特的和个别的东西的静观极力要直觉地掌握历史中的‘普遍的’观念、‘趋势’,即‘客观的’观念。” 美国与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 TheImageofRankeinAmericanandGermanHistoricalThought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GeorgG.Iggers 何兆武、黄巨兴译 原载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GeorgG.Iggers,"TheImageofRankeinAmericanandGermanHistoricalThought",inHistoryandTheory,Vol.2,No.1(),pp.17-40. GeorgG.Iggers 在德国和美国的历史思想中,兰克的作用之大是我们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从年出版他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其中包括一篇著名的附录:《对于近代史作家的批评》)到现在,兰克对德围史学一直是大有彩响的。同样,自从19世纪末专业历史学兴起以来,兰克显然对美国历史思想也产生了影响。不仅许多19世纪的历史大家,如魏兹(Waitz)、吉塞布雷希特(Giesebrecht)、达尔曼(Dahlmann)、班克罗夫特(Bancroft),都是兰克的弟子;而且其他许多人,如美国把历史专业化的赫伯特?亚当斯(H.B.Adams)、布恩(E.G.Bourne)、柏哲斯(J.W.Burgess)和奥斯古德(H.L.Osgood)以及德国学者像迈纳克(Meineke)和特罗尔什(Troeltsch),也都受过兰克的教育。的确,差不多每一种有关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方法的德国历史思想或美国历史思想的重大讨论,都集中在或至少牵涉到是接受还是拒绝兰克的历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问题。因此,兰克的形象在19世纪末德国的实证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论战中就成为了一个中心问题,兰克变成了20世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重要的思想鼻祖。到了纳粹以后的时期,迈纳克号召通过重新检査兰克的办法来重新检査一下德国历史著作的传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这种重新检査的过程中,德国历史学家出版了自从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死后的最大量的有关兰克的书籍和文章。同样在美国,历史学家也认为必须确定兰克的位置》19世纪末的“科学派’’(scientificschool)企图把它对于兰克方法的概念作为历史学丁.作的基础。“新史学”(NewHistory)和相对主义者的反抗,开始于鲁滨逊(Robinson)和贝克尔(Becker)大律宣传反对wieeseigentlichgewesen(“如实直书”)这条金科玉律。所以,研究德国和美国历史思想对兰克的解释,其意义就不仅只是理解兰克的思想而已。基本上说来,德国和美国历史思想的历史不仅能够、而且应该由历史理论家针对着是接受还是拒绝兰克这个问题而制订出来。 此外,兰克本人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对史学的发展还比不上历史学家心目中兰克的形象那么重要。兰克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比起他作为一个是被人接受还是被人拒绝的标准的化身来说,影响要小些。这里所说的标准,包含历史方法论的基本理论和对历史研究范围的基本态度。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在美国占优势的兰克形象和在德国流行的兰克形象根本不同。大约在兰克去世的时候,在美国发展出了他的一幅图像,而在德国又发展出了他的另一幅图像——后者大体上差不多是所有的历史学家、兰克的弟子和评论家都接受的形象,也是几十年来相当稳定而没有变动的形象。美国历史学家因为不能够理解兰克的历史思想的哲学意义,就把兰克对文献的分析批判(这是他们所理解的,也是适合于他们陚予历史以科学的荨严所需要的)和兰克的唯心主义哲学(这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分裂开来了。然后他们把这种批判的方法和讨论班的组织移植到19世纪末美国的思想园地。这样一来,兰克就被几乎所有的美国历史学家(包括“科学派”历史学家、“新史学家”以及相对主义者)尊为“科学派”历史学之父,被认作是只注意于确认亊实、特别是在政治和制度领域中的事实的一位非哲学的历史学家。但是在德国,兰普雷希特(KarlLamprecht)却在实证主义的旗帜之下大肆攻击兰克,说他是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这是一种基本正确的解释,这个解释得到了兰克的卫护者(如迈纳克)的完全同意。因为德国历史学家和他们的美国同行不同,是了解兰克思想的唯心主义的根源的:对于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兰克变成了非哲学的经验主义的对立面。他们深深知道兰克通过对于独特的和个别的东西的静观(Anschauung)极力要直觉地掌握历史中的“普遍的”观念、“趋势”,即“客观的”观念。因此之故,说来像是讽刺,兰克起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在美国,他只是部分地被人理解,却被当作是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路线的思想始祖;在德国,他却被当作是新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一种灵感的源泉,新唯心主义历史学家是反对西欧历史学家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的。只是在过去十五年间,美国历史学家——其中包括一些徳国流亡的学者——才开始认真地重新检査在美国历史思想中已经成为了传统的兰克形象的问题,并且得到了和德国历史学家更加相同的对于兰克的见解。 一 非常有趣的是,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Bancroft)是兰克讨论班上的一个学生,但是他并没有把兰克塑造成美国的形象。反而是新一代的专业历史学家把这位代表研究广泛主题的叙述性历史学传统的班克罗夫特看成是一个非科学派的历史作家。 对新“科学派”的历史学家来说,班克罗夫特当然是非兰克派的,即使兰克本人曾经称赞他的这个学生是“民主派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这些新“科学派”的历史学家在一个信赖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时代,迫切地要赋予这种新的专业以学术的尊严。有些历史学家——比如怀特、费斯克、亚当斯兄弟,他们都受过孔德、巴克尔或者达尔文、斯宾塞的彩响——把科学的历史看成是对于历史的过程应用一般规律,好像应用自然科学上的普遍规律一样。但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历史著述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客观地建立史实的方法,所以把兰克奉为“历史科学之父”。这样一来,历史科学的定义就真的和兰克的方法完全是一回事了。这种概念看起来是美国所特有的,而不是从英国历史学家那里继承下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宣称兰克是他们的导师,这在思想上也是诚恳的。或者,有一个困难是从科学(Wissenschaft)一词的极其不同的概念之中产生的,德国不像美国,从来没有把科学一词和自然科学联系得那样密切,它只是意味着用系统的方法来进行任何一种研究。这些美国历史学家有几个在徳国留过学,做过兰克的学生;至少,奥斯古德听过兰克的讲课。但是他们对兰克的理解是有选择的。他们抓住了兰克对资料分析批判的重视,所以把讨论班的方法介绍到美国大学里来。但是,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们曾广泛地读过兰克的著作,也没有一点证据表明,他们曾看过兰克的为数不多的理论文章,比如说《政治谈话》(PolitischesGespraech),或者是收在《全集》(SammtlicheWerke)第53-54卷中多斐(A.Dove)发表的信件和断片。自从这位德国大师在年退休以后,他们也没有去和他谈过话。而兰克的形象正是在美国历史学家的这个小团体——在年只有二十个历史教授的职位——之内具体化了起来的。在约翰·霍普金斯研究集刊中发表的几篇关于历史方法和讨论班的文章、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出版物以及在赫伯特·亚当斯和布恩写的两篇论兰克的重要论文中,兰克的形象得到了系统的叙述。“科学派”历史学家只是或多或少地在正确领会了兰克的分析批判方法的某几个方面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史学的理论,这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兰克的理论。 美国历史学家在当时对兰克的方法和他的历史观所作的种种解释是特别一致的。密西根大学的査理·亚当斯,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赫伯特·亚当斯,耶鲁大学的布恩和哈佛大学的艾默顿(EphraimEmerton),在关于历史教授法的各种论文中,都认为兰克对讨论班(Seminarium)(即他的训练未来的历史学家的方法——也就是尼布尔[Niebuhr]和古典语言学家所用的考订文词的谨严方法)的改造,不仅对于德国史学而且也对于美国历史的科学著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他们全都认为兰克的客观性——他们把它和历史科学方法看作是一回事——是通过对原文的分析批判而集中到史实的建立上面的,所以他们相信对历史进行的一种兰克式的研究(即科学的研究)就在于寻找事实,而很少或者不必注意概括,同时要严格地撇开一切哲学。因此,赫伯特·亚当斯写道: 尼布尔(Niebuhr)虽然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史料考据家,但他却以形形色色并没有为现存的证据所证明的关于道德的见解和哲学的见解来阐明他的罗马史。……兰克与此相反,他一心一意地紧紧抱住历史事实,不加说教,不用教训,不讲故事,而只是叙述简单的历史真理。他的唯一的心愿是如实地叙述事实——“wieeseigentlichgewesen”(如实直书)。真理和客观是兰克最高的目的。根据他的意见,历史不是为了遣兴,也不是为了教导,而是为了知识。……他不相信表明人类历史中的神意是历之学家的本分。(《论兰克》) 艾默顿发现兰克是“真正的历史方法学说”的创立者,所以评论道: 如果一个人要在一个以精神为其主要特征的历史学派和一个以得到最大数量的文献事实为根据的历史学派之间加以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老是踌躇了。……科学训练已经代替了华美词幸的地位,今天全世界都受益匪浅。(《实用高等历史教授法》) 在年,乔治·亚当斯(GeorgeB.Adams)在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发表的主席演说中,反对社会科学家的日益剧烈的攻击,企图团结传统上的科学派历史学家来响应“我们第一个领导人的号召:历史学家的第一个责任是实现‘如实直书’的叙述”。他说: 如果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的行为是受规律支配的吗?我们发现这些规律就能够建立像化学成为一种科学那样的一门历史科学吗?这是一回事。但是要问:严格的科学调查研究的方法应用于人类过去的行为,能够使我们更加确实地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吗?则全然是另一回事了。兰克学派从来没有想超出这个最后的问题的范围,而兰克学派对这个问题一直是作了明明白白的(我相信也是无可争辩的)肯定的答复。真正的结果是,一种调查研究的科学和一种训练历史学家的方法已经完完全全地统治了历史学界,——这种说法是并不过分的。无论怎样,所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五十多年以来千真万确地是按照这些思想接受训练的,他们全都感觉使自己从他们的学派的这样一条基本原則之下解放出来是极为不易的:历史学家的第一个责任就是尽可能地肯定并精确地记录下来所发生的事实。不大可能发现,经过这种训练的历史学家会比早些时候的其他前辈更加专心致志于研究科学的问題或者历史哲学的问超。所以,事实是直到现在,专门的历史学家还不曾研究这些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題留給诗人、哲学家和神学家去解决了。(《历史和历史哲学》,载《美国历史评论》) 的确,有些作家如约翰?林肯(JohnLarkinLincoln)(布朗大学的拉丁语学家,兰克的弟子,学术界老前辈)、斯塔肯堡(J.H.W.Stuckenberg)(柏林美国教会的牧师和社会学家)、马汉(AlfredT.Mahan)都认识到:兰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超出了为事实而搜寻事实的,但是一些主要的研究部门的人们却相信兰克整体上的非哲学性。所以,布恩在一篇评论那尔班田(Nalbandian)的研究的文章中(尽管那尔班田分析兰克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篇材料很不错而论述又精彩的文章),却依然表示“惋惜说,作者并不曾同样留心地既考察他的方法(作为一个调査者),又考察他的意义和影响(作为一个教师)”。 对所谓“新史学”——它是把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的全部活动拿来考虑的,并且是“以现在的社会利益具体地在表现过去”的——的需要,还在鲁滨逊(J.H.Robinson)于年出版他的著名论文集《新史学》(TheNewHistory)以前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种很大的潜势力了。早在年,透纳(FrederickTurner)业己写道:“历史是一切传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仅是文献而已,所以,“新史学”这个术语本身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问世了。 “新史学家”在号召历史学应该超出事实而走向归纳和概括的时候,是在向兰克的方法论,更正确地说,是在向“科学派”所保持的兰克的形象挑战的。他们承认“科学派”自命为兰克学派的这种说法,并且大部分还接受了老一辈把兰克看作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非哲学的作家这一形象。这样一来,他们就特别反对兰克被人认为未能超出事实而进行概括的缺点?哈特(A.B.Hart)在他的主席演说中,对美国历史协会全体会员宣布:兰克曾天真地假定说,历史学家只能够“单纯地告诉你事情是怎样的”鲁滨逊论述了兰克骄傲的自夸,即他所提出的要说出真相来——“如实直书”,并指出他并未能认识到分析批判的方法只是替科学的历史学在作朴素的准备罢了?。至于在班兹(H.E.Barnes)看来,兰克的贡献主要是,“他总结了内部考据的各种原则和在讨论过去时坚持完全客观”?。兰克要求“我们应该正确地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绍特韦尔(J.T.Shotwell)说:“兰克所发挥的理论,其含义只不过是要把过去栩栩如生地重新表现出来而已。”他所关心的是“具体的、明确的事情,搜求各种细节,警惕着自己掌握材料的主观性而保持客观性”?。对提加特(F.J.Teggart)来说,兰克代表的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那时的科学所从事的乃是积累事实,而不是归纳。“总而言之,兰克思想的偏好和他所处的时期,都早于达尔文生物学的时代。”(《历史学的情况或梗概》,载《美国历史评论》第15卷) “新史学家”对老一些的兰克形象所作的一个修改,大概是对兰克概念的改变,认为他纯粹是一个静态的历史学家,其主要兴趣仅只在于细节的叙述而不在于对发展的研究。这一点却反映了这些学者对兰克的著作读得非常之少。经常提出来的新的战斗口号(大概是从兰普雷希特那里借来的),现在已不是“wieeseigentlichgewesen”(如实直书),而是“wieeseigentlichgeworden”(按事情是怎样演变的)。 令人惊异的是,美国历史学家的兰克形象受到兰普雷希特的影响非常之小,而兰普雷希特在德国花了二十年的时间领导着一场修正史学史的运动,它采取的途径和美闻“新史学”所采取的一样。兰普雷希特于年在美国讲学。只有一个不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厄尔?道(EarleWilburDow),似乎对兰普雷希特的著作仔细渎了一番,结果写了一篇文章,对兰克的形象作了一番重要的修正,可惜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厄尔?道在一篇评论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的文章中,虽然承认考证学的价值,但是他强调这种学术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对(历史学)以及对其他几种社会科学来说,都是如此”。厄尔·道认为,历史学是一种归纳的科学。但是,在他看来,兰克并不真正厲于老派的专门学术之列。说得更恰当一点,兰克的历史观是以形而上学的前提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按照兰普雷希特的说法)它是德国Identitaetsphilosophic(同一性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一种普遍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上和德国古典文学中世界主义的历史观一样。兰克意识到有一个隐藏在世界背后的上帝,上帝通过人类和历史来表现自己,所以兰克就把个人、民族和国家描绘成为一种世界运动的工具。“思想”、“传达力”、“更高的权势”、“推动世界前进的活精神(Geist)所产生的力量”——这些,按照兰克的描述,当它们展现时全都能为人们所察觉,但却不能加以界说。厄尔?道在结论中说:“从这里面要发现很多现代的科学精神,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不管对兰克的评价是多么高,但他总归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儿。” 在相对主义者和新史学家之间要清清楚楚地划出一条分界线是很闲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贝克尔和贝尔德两人在传统上都属于“新史学”派,因为“新史学”是通过广大的、社会的途径来研究历史的。基本上,“新史学”里面就埋着相对主义的种子,因为它把历史的认识看成是一种连续不断的、以社会为条件的过程。透纳早已说过每一个时代都根据它那个时代最突出的条件重新编写过去的历史。或许,相对主义者和新史学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就是贝克尔的怀疑主义和贝尔德(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年)的怀疑主义了,后者认为甚至于接近客观的知识也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相对主义的争论中,兰克的形象起了主导的作用,而这种形象根本上乃是“科学派’’的兰克的形象。 贝克尔在年发表他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演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篇演说第一次使他的观点名噪一时,二十年以前,他就已经始终一贯地宣传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主义的立场了。他在年打了第一枪,那就是他发表的《论漠不关心和历史著述》的论文,这篇论文是针对兰克派主张客观的史学根据“如实直书”描写过去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幻想而发的。两年以后,贝克尔又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问題和思想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影响的几个方面》的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历史学在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成为‘科学’,这受兰克的影响也许不下于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但是,贝克尔也认识到,美国“科学派历史学家”在“对于历史事实采取一种像科学家对自然现象那样的客观和超然的态度”方面,或许比他们的老师走得更远,他们的老师尽管抱着不偏不倚的高尚理想,却不曾完全从唯心主义的前提之下把自己解放出来。 不过,兰克作为经验主义的、非哲学的历史学家这一形象,也许在贝尔德和史密斯(T.G.Smith)论战的文章中得到了最明显的总结。贝尔德在他的至今还脍炙人口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写作历史是一种信心的行动》(发表于年)中认为,当代思想已经抛弃了兰克所创造的这种概念,即“可能如实地描述过去就像是工程师讲解一架机器一样”。这种客观性的理想,只是与兰克有关系的徳国统治阶级旨在巩固他们的地位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史密斯则为“兰克公平无私地追求真理的思想”而辩护。所以贝尔德在回答他的这种辩护时便进一步检査了“兰克的历史公式”,并发表了一篇題为《那个高贵的梦》的文章。“历史的真相,经过考证研究,能够被揭示出来,能够被当作是客观真理,也能够如此这样地加以叙述”,——这一理论是以某些假定作为依据的《其中包含这样一些信念:“历史学家至少为了达到他的研究和著述的目的,能够摆脱他本人的种种兴趣的色彩,例如宗教、政洽、哲学、社会、男女、经济、道德、美术等等,而且能够极其公正地考虑这类Gegenuber(对立面)”,“历史学家通过纯粹理性的或者知识的努力,就能够理解这种历史的本质自身,同时这些本质的东西,既不能渗透着、也不能夹杂有任何先验的东西“。兰克确实“在事实上并没有跟着他这种推论的逻辑得出经验主义的结论”,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了宗教的和政治的偏见。“他虽然抛弃了哲学,宣布了实证的历史学,但是仍然受着Pantheisrnus(泛神论)的约束。”贝尔德的《史学史中的思潮》这篇文章反映出,虽然他读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历史主义者(historicist)的著作,但一点也没有根本改变他心中的兰克的形象。 史学史的其他作家在过去二十年之中,一直都把兰克学说的精髓等同于这条金科玉律:wieeseigentlichgewesen(“如实直书”)。汤普孙(JamesWestfallThompson)在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历史著作的历史》中主要也论述了兰克对资料的考证性的处理。虽然他对兰克的思想学说讨论得极为简略,但他的结论仍然是:“对兰克以及对‘客观的’和‘科学的’兰克历史学派的主要批评(在于)其整个的非哲学性。”(《历史著作史》第II卷)尼文斯(AllanNevins)认为兰克是“提倡无色彩的历史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历史思想曾被很好地总结为有口皆碑的一句话:叙述过去应该wieeseigentlichgewesen(“如实直书”)。尼文斯和汤普孙两人在提到贝尔德的《那个高贵的梦》时指出:尽管兰克的理想是客观,但兰克**并没有做到完完全全的客观;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不自觉地站在他那个时代普鲁士的保守反动的立场上写出来的”。霍尔特(W.StullHolt)在他的一篇杰作《美国的科学历史学的思想》论文中说,美国科学学派的理想就是兰克的理想。贝提(E.C.O.Betty〉和约?史密斯(JoePattersonSmith〉(在《纪念马可?哲内甘的美国史论文集》中)、内夫(EmeryNeff)(在《史中之诗》④中)、哥特肖克(LouisGottschalk)(在《历史的理解》中)以及约迪(WilliamH.Jordy)(在他的评论亨利?亚当斯的一书中),都反映了一种类似的解释。最近,韦伯(WalterP.Webb)作一篇文章中提出批评说,美国历史学家(由于把德国讨论班的实质看成是教学的方法而非其所表达的伟大的思想)所移植过来的只是它的外壳,而不是它的内部的精神;尽管如此,他依然描绘兰克说,“他的名宇是‘科学的’历史学方法的同义语”,并把兰克描绘成为属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传统的人物。兰克“是和莱伊尔(Lyell)、华莱士(Wallace)、达尔文和雷南(Renan)同时代的人,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运用了分析批判的方法,而且最终作出了惊人的成绩。他(兰克)把教室变成了实验室,用文献资料代替了‘大量的蛤蜊’”——这就是韦伯对兰克的评论。 二 在德国,出版论文和书箱的高潮是在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最初是在兰克九十岁大寿的时候,然后是在他逝世的时候。这一潮流的出现和美国的兰克热是间时的。然而德国对兰克的讨论和在美国的不同,它表现为一股稳定的潮流而一直持续到今天。值得注目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卷帙浩繁的文献,正如傅特尔(Fùeter)所指出的,都把兰克处理成为一个历史理论家而非一个历史写作家。 兰克的形象在80年代以前,并不曾确立。对于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没有系统研究,而只有一些零星的评论,其中有许多都是带有争论性的。“如实直书”这一信条以及兰克所明白表示的要在自己的作品里消灭主观随意性这一愿望,在一般人对兰克的印象中还没有清楚的轮廓;大家知道,他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并且是第一个把语言学家和古典学者分析史料时所发展的那种考据方法引用于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人。“客观的”历史学家这一形象,更被黑格尔派与民族主义派的兰克批评者所加强了。据说黑格尔本人曾经说过,兰克只“不过是—个平凡的历史学家”,而利奥(Leo)和其他一些人则攻击兰克对于细节与真情实事的学究式的 |
当前位置: 个旧市 >格奥尔格middot伊格尔斯美国与
时间:2018/7/3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红河州妇幼保健院个旧市公安局招聘啦快
- 下一篇文章: 个旧这名男子经常打老婆这一次,法院介入
- 热点内容
-
- 没有热点文章
- 推荐文章
-
- 没有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