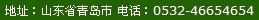|
难怪人都说自己的家乡好,因为家是送别时的背影,风雪的归程。家乡是未改的乡音,永恒的思念。 东大墙,是我的家乡。“东大墙”三个字,字字高大坚强,擎天撼地,气宇轩昂。行政属周至县、竹峪镇、东大墙村。地处青化镇、哑柏镇、竹峪镇的“金三角”地带。东大墙也叫竹峪东堡。竹峪东堡又分为老堡子、新堡子,我就是老堡子人。 苍天之于东大墙这块丘陵,南北长五六里,东西宽均约一里,地势从南向北倾斜,周围与佛探头、赵家梁、任家台、西大墙、竹峪沟、解家口、胡家湾、白村连畔种地。站在这二道塬上,向南仰望,秦岭逶迤20余里,依附于大山的怀抱;东与仰天河水库相伴,滋润着水的化合物;西被一条大深沟簇拥,旖旎的风光仿佛一片世外桃源;向北俯瞰,绵绵渭水藏匿于渺渺茫茫的云染之中,极目处会给你带来无限的遐想。 在远远近近的七沟八梁中,大自然孕育了这块独特的丘陵,它以博大、旷远、坚韧的姿势,展示着龙的身躯,描绘着不能诠释的全部。 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块丘陵雕成一条卧龙。龙的头部、身姿、肩胛骨、尾巴和四肢形象逼真,活灵活现,栩栩如生。龙身从南向北盘踞;在北塬上地势升高,像是龙在抬头;沿着赵家梁向南延伸,像是龙在晃动着身子,尾巴向西南摆动;四条出村大路,向外向下伸展,像是龙的四只爪子,深深地插入三秦大地。这条沉睡的龙刚刚苏醒,抖抖身躯,准备腾飞。梦想紧随中华巨龙,“扶摇直上九万里”,飞向明天,飞向世界,飞向幸福!东大墙就座落在这条龙背上。 袅袅炊烟,点缀着东大墙村庄的落迁。东堡子、西堡子隔沟相望,东大墙、西大墙更加昂扬。据飞仙沟喻振才老先生撰:“周文王擂鼓台练兵,为遮掩扶风召村的商纣王敌情,而建东、西大墙”,村名故而得之。历史近则明、远则暗,两座大墙谁能说清矣?恕我浅见,东、西大墙是以城墙而命名。周文王擂鼓台练兵暂且不谈,一则拉直擂鼓台与扶风召公村(法门寺向东14公里)的视线,东、西大墙方向东偏甚远;二则东、西大墙距擂鼓台与召村两点一线的高差,低至于百米之上。建这么高的土墙,岂非天方夜谭? 据《周至县志》记载,明清年间,关中多年灾情,百姓四处乞食。为防宵小之徒,有条件的村落,靠拢群居,建城墙而御之。历史演绎先有城墙,后有堡、屯、寨。 经考证,多年前,东大墙的老堡子从老机井西南迁址现在村西北米的大深沟边。先筑城墙,故称“老堡子”。城墙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80米,城翁池住24户,一个大涝池,两口水井。南北两条街道,分南排、中排、北排子。大城门朝东,城外北侧有座大石碾,一棵大槐树。这棵大槐树是老堡子的象征。这座城墙孕育和陪伴了我的成长。我孩提时代时,在那城门外脚部的碌碡上揉泥球;春节爬到城门拱顶瞭望室取锣鼓家伙;帮大人推碾子,砸辣椒、碾腊八;在城门口玩弹球、打弹弓、滚铁环、挖渠渠、捉迷藏、抓坏蛋;爬到城墙上摘构桃,偷城墙西南角杨姓家的杏……20世纪70年代,老堡子在先贤淡世昌队长的带领下,全村向南扩移多米。 新堡子后筑城墙,故称“新堡子。城墙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70米,城翁池南北一条街,分东西两排子,住28户,两口水井。大城门朝北,城门外西侧是个大涝池,东侧有座大石碾,一棵大槐树。这棵大槐树是新堡子的象征。至今这棵古槐仍以魁伟的身姿,婆婆娑娑,枯枯荣荣,依如旧往地坐阵一方,牵手着后人,传递着城墙的历史。 20世纪60一80年代,两座大半垛城墙和老堡子的大城门,先后失迹。我怀念那座古老的城墙,虽残垣断壁,斑痕累累,但在那敦厚有力的身躯上,透视着东大墙的历史;虽个头不高,更不延绵,但在那冷艳的血光里,映射出祖先的持重和气节;虽帐然若失,杳无踪迹,但在那无影的骨子里,彰显着强宗固族,振我村声的豪迈气概。在寻找家乡的最好印记中,城墙多了一层认知的东西。城墙是我的摇篮,城墙是一个永远看不透、讲不完的故事。 成长中的故乡,藏匿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着内在的意义。人民公社期间,东大墙归建于新兴大队,老堡子为一队,新堡子为二队,胡家湾三队,白村四队,佛探头五队,赵家梁六队,杨家庄七队,王家挡八队,岭梅九、十队。其中老堡子42户,多人;新堡子80多户,多人。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改革开放,东大墙脱离原新兴大队,于年成立东大墙村委会,土地承包到户。老堡子为一组,新堡子为二、三、四、五组,胡家湾为六组。迄今为止,老堡子户(淡姓为主体,62户),人;新堡子户,人,计人。可耕地亩,人均耕地一亩挂一二。 “麦子天授,不论贵贱贫富一同滋养;麦子地予,无论百姓皇上同食同享”。余甚喜,家乡的大面,难怪周至人为竹峪、翠峰的麦面颂赞。食之,有回儿时乡野之念,犹卧大场闻麦之乐。秋日时分,大雁成群两行,检阅着牛拉弯犁,农夫扶辕,俯首耕耘种麦的场景。冬日微霜,麦苗蓄藏,春日荡漾,夏日金黄。收割季节,丘陵人提前上场,磨镰励石上,挥舞割太阳,人畜齐上场,木掀把麦扬。每年碾麦时,生产队就要炸油饼、吃油条。油烟笼罩着锅台,清油在锅里翻滚,油香弥漫着天空。在那外焦里生的油饼里,农家人尝到了一年的酥香和美味,手上芬芳;吃大面时,旱塬人眼角的笑意,一直延伸到心窝里,盈香柔长;手举参菜、参玉米面的馍馍时,洋溢着收成的喜悦和激动,齿颊留香。然而颗颗麦粒也包含着伤感的情愫,东大墙的麦子亩产斤左右,2/3上交国家,余粮勉强维持半年,这就是当时那个年代社会主义农业的主旋律。 “人有沟壑万千,难言其中一二”。从古到今,苍天赋予东大墙这块土地人多地少,在那黄土单调的颜色里,“俯畏人言,仰畏天命”。20世纪60年代,水是东大墙人的眼泪。“黄金有价水无价”,水是生命之源,农业的乳汁,人类的命运。如果人离开了水,你可想而知矣?过去东大墙仅有七八口吃水井,每口井深40多米。用木辘辘搅水,强力者一人方可,弱力着两人搭挡。人吃水都困难,那还谈得上用水浇地呢?记得小时候生产队栽红薯,我那挑水的热情,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平日男劳一天10分工,女劳一天8分工,我干一天4分工,栽红薯挑一担水1分工。当时从南沟挑水栽红薯,要爬行徒坡一里多路,每天我可挑10多担水,要挣10分多工。那时挑水的心情不仅仅是激动,而且也是劳动的封赏和一种心里平衡;不仅仅说明“水贵如油”,而且也充分证明了我小时那吃苦耐劳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清晰地记得,年东大墙为解决土地浇灌问题,曾将泥峪河的水,引渠到东大墙的老机井东侧。淙淙小溪中,一股浑浊的黄泥水,像远处飘来的绸带,刚到地头就断流了,原因是上游截流。无数个劳动日付之东流,“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东大墙人空洞的眼神,凝望着暗淡的天空,只能望穿雨水。 旧貌换新颜,让落后成为过去。年政府给东大墙打了第一口机井,后又陆续打机井8眼。年铺设地下浇地网管米,水浇地达到了全覆盖。自来水到家,流进厨房,冲刷水厕。全村水泥路面贯通街道,沿至各户门前,满足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尤其是近几年在国家扶贫开发战略实施中,西安“中铁一局”常驻扶贫干部3人,忽略家庭,常年驻村。先扶思想,强化内生动力,“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励志奋斗。后精准扶贫,开发合力。今年,扶贫工作组为建出村路担责征地,由政府出资,打通了村子通向环山路的水泥路,实现了东大墙出村不爬坡的千年梦想;完善了3口机井变压器、高压线路的基础设施改造;拓宽生产路0多米,改善了村容村貌。工作组还为胡家湾改建、修建了自来水柜和文化广场,安装路灯60盏。携力东大墙即将脱贫走向小康! 踮起脚尖穿越时间的经纬。曾经的东大墙,涉过生命的万水千山,时至今日终将可以在此。曾记否?秦岭北麓二道塬上的先祖,在饥饿中寻找着生命的加持。20世纪80年代前,诸如周家堡的人编草鞋,陈家堡的人编粪笼,东大墙的人编背笼等。 千百年来,竹子一直被人们称赞。文人咏竹、赋诗,是吟唱竹子的妙娑、骨气、神韵和美好的寓意;东大墙人颂竹,是称道竹子给予了生命的加生。以前的东大墙人都会“编筐筐、卖笼笼”,也就是用手编制竹器物。那时做竹篾活,大有全家动员之势,亦是男孩子们的必修课。我很小时就跟着大人买竹子、划篾,先学编汽馍筛筛,后学编背笼。手艺高的人编小提笼、膛笼(船型竹提篮),还有能行的人编鸡笼、牛笼嘴、竹笼管、竹耙子等。尤其是新堡子巧匠徐姓生魁公,用秦岭深山的毛竹,编制的大笸箩,独树一帜,远近闻名。每逢农历三、六、九,东大墙的男女老少,成群结队,迎着清晨第一缕的阳光,带着劳动成果且又未能喜悦的心情,手提的、肩挑的、自行车推的、架子车拉的各种竹器物,赶哑柏镇的集会。在哑柏北大街的路两旁,沿供销社、药铺子、裁缝店、铁匠铺、照相馆、食堂和民宅门前的台阶下,竹器物形成了两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公路两边摆卖时,还不时地巴头伸脑,窥探着“死脑筋”扑来规范市场,弄不好就被他将卖的东西踩坏。还有那么几年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共产风吹起了破碎的流年,东大墙的人站在伤心的角落,无处倾诉,长吁短叹也! 生存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东大墙人在自然与现实的夹击中,毫不退却,永不懈怠。在多少个刀刃不卷的篾刀中,在多少个旧球鞋的橡胶皮张上,在多少个深夜的煤油灯下,去迎接朝霞,奋斗生活。也为周至县城农历二、五、八,武功县长宁镇农历三、六、九,眉县农历单日、槐芽农历双日的集会上,送去了民生,繁荣了市场。 竹子,也为多少代的东大墙人收获了业绩,战胜了困苦,笑纳了满足。遥想先祖为传承血脉之坎坷,缅怀先祖为了糊口之功绩,东大墙的后辈子孙们,应从竹子身上领略它的超凡和魅力,读出艰辛与沧桑,悟出启迪和真谛! 在多情的夕阳下,走进忆想的巷口,不曾抹去的苦涩,漫卷整个心扉。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有多少个东大墙人,为了强烈的生存走进深山,去寻找着比干竹器活更大的经济效益。我从13岁开始就跟着大人上山割柴卖柴,泥峪河偷木头,周佛公路拉扫帚……曾经的汗水和泪水,每粒都那么的滚烫,不时地滴在心里;曾有多少个东大墙人,背着刺绣串街走巷,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曾有多少个东大墙人,为了生计,倒金贩银,铤而走险等。这骨感的现实,无奈地宿命,挤扁了人心。 粮食是“母亲产业”,果木是“致富产业”。20世纪90年代后,周至县西南地域培育改种了猕猴桃产业。秦岭北麓的猕猴桃产量位居中国第一,说是猕猴桃产业基地,还不如说是享誉全国的“猕猴桃之都”。东大墙及周围二道塬上的猕猴桃质量,位居中国第一,尤其是亚特、翠香品种。外皮果胶丰富,果肉丰满,口感香甜。究其原因,猕猴桃的质量与地球经纬度、海拔、风头和土层密切相关。年,有“心连心”独家冠名,想全国“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大赛中,东大墙摘得猕猴桃“丰收王”桂冠。近几年周至人为猕猴桃的更新换代提供了不懈的努力。东大墙先后培育和引进了秦美、亚特、翠香、海沃德、华优等优良品种,形成了主副产品层次分明,果肉色泽各异,早中晚熟,合理搭配的多样化产业格局。年逢十月,猕猴桃挂满枝头,果实累累。北风何骚骚,憨憨塬上人。丘陵沸腾了,寄予的年收期于眼前,人们在可掬的笑容里,掩饰不住丰收的喜悦和希望。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乡的传统民俗是庙会。过庙会是由竹峪八堡(东大墙老堡子、新堡子,西大墙,竹峪沟东、沟西,半个城,韩二台,任家台)一起祭拜太白爷。年逢农历正月初九是太白爷的庙会,这是一次传统习俗与春天的约会;农历七月十三是太白爷的生日,这是一次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教育。庙会以八个堡子轮流坐东,时隔几年就要给太白爷唱一场大戏。过庙会时,八个堡子抢先上阵,威风锣鼓,跃动山川;彩旗飘飘,迎风招展;秉烛焚香,鞭炮燃放。祈福太白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倡孝扬善,百姓安居乐业等。从年始,因新冠疫情太白爷庙会,由原来每年两次减为一次,定在农历七月十三。太白爷庙座落在东大墙西侧沟东,坐东向西。庙内立坛三尊神像:太白爷、瑶池老母和送子娘娘。在神像容颜的流光里,震颤着竹峪八堡多少代人的灵魂,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笔步太白庙,一怀浮想随风逐来。“文革”前,我就读小学于兰梅塬。路途六七里,且要翻越东西大墙的深沟。路过太白庙,擦身水打磨,穿过芦苇荡,跨过流水桥。在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上,雨雪天光着脚丫,拄着木棍。冬晨打着麦草火把,驱赶着禽兽野狼。在上学的路上,听见了犬吠、蝉鸣、蛙叫;看见了鸽群、老鹰、野兔……在土坎的杂草中,小枣子显得格外强悍,摘颗金灿灿、圆溜溜的小酸枣,仔细咀嚼起来,酸甜味似乎多了几份向往,也似乎多了几份酸涩。有时雨雪天路滑时,偶尔向南拐到瓦盆窑的路上,钻进土窑洞里去躲雨,在哪儿我倍感到土窑洞那独特的黄土地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两个瓦盆窑不见了,无数个土窑洞也分别渐渐地远去。但是在人们的印象里,它依然是部史书,记录着沧桑的岁月。 东大墙的一个亮点是天主教堂。教堂与太白爷庙地处南北俯仰相望,携手牵引着周围百姓的宗教信仰。村中13户的天主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信教徒们去教堂祈祷,在默声诵读中告诫人生向好、向善、向荣。抛弃丑恶,信从道德。用内心定力去敞开心扉,驱散人心中的黑暗,走向美好明天。我曾去过西欧罗马梵蒂冈,那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领土面积0.44平方公里,人口。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信仰中心,领导着全球宗教信仰占比最多的天主教会。梵蒂冈教堂仅从建设到装修共用了年,其壮观程度,真是令人堂目结舌,心驰神往。当然远方之所以让人向往,正是因为那里有太多未知的东西。东大墙的天主教堂建于0年,长27米,宽12米,面积平方米,容余人。教堂在寸土尺地的力争中,有个超大的院子,设有食堂,大铁门朝南。这座宏伟的天主教堂,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竖立于东大墙的西方,仰望着梵蒂冈。教堂以顶上的十字架、穹顶玻璃窗、讲台和一排排的桌凳,展示着教会的荣耀、教化和激励。 东大墙的标志是文化广场。党支部、村委会、学校、幼儿园和体育设施等,座落在东大墙西侧的空闲地带上。天主教堂、村委会和学校三足鼎立,文化广场依附于三点内侧。在一片宽敞的水泥地面上,设置了篮球场、乒乓球台和各类锻炼器械。晚饭后,夜色包围了村庄,荧光路灯无力地照着大路、街道和文化广场,驱散了村庄往日的寂寞和天黑时的恐怖。人们三三两两走出家门,在路灯的陪伴下,在文化广场随着音响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 新学校重建于年,现开办公立幼儿园。我怀念那被村委会坐在屁股后面而躲藏起来的小教室,沉醉在优美的境界里。在那曾经简陋的小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是那么的整齐、歌声是那么的嘹亮;在那曾经的操场上,留下了我们跑早操、打垒球、做体操和玩耍的身影;在那曾经的学校里,一个教室两个班,两个班一名老师,捧着语文、算术两本书,掀开了知识的大门。沿着学校铺设的土路,走出了浙江大学医学博士淡松松,赢得了丰盈的人生。他利用在校期间打工挣的20余万元,连续四个春节回乡举办立心公益活动,以最浑厚的呐喊,激励着有志之士,招手未来与成功! 在村人的鼓励下,拙笔“东大墙”,兴致虽盎然,文墨却粗通。远古的故乡,是一本读不懂的书。我辈的家乡,尽管一览无余,但在吾的笔下却敬畏不知所云也,只好竭力记录一二。在低头的回忆里,落日与朝阳一样行走,青春与暮年一样美妙。愿我的家乡在龙的呵护下,去迎接挑战,迎接美好,迎接辉煌! 年4月13日 作者简介: 淡乃智,陕西周至人。从戎新疆炮兵27年,正团转业西安工商。 在部队曾进3个院校深造。撰写刊发稿件20余篇,其中《沙漠地火炮射击》一文,被中科院载入《中国军事文库》,并授予个人著作权和暑名权。荣立三等3次。 在西安工商负责《工商理论研究》,刊载论文90余篇。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gejiuzx.com/gjsxw/13787.html |
当前位置: 个旧市 >周至走不出你的视野记我的故乡东大墙
时间:2023/3/12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国产威士忌的角逐,谁将成为中国的山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