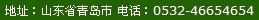|
中科白癜疯口碑怎么样 http://nb.ifeng.com/a/20180331/6472849_0.shtml 天上紫薇垣,地上紫禁城。 紫禁城故宫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年)。年,紫禁城建成年整。 年10月10日,故宫首次对外开放。在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上,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在场的市民说:“从今日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从此,关于故宫的故事不再只是历史书上的年表,河流的主干开始容纳一条条细小的支流,在不同的人生活中映射出不一样的紫禁城。 值此紫禁城建成六百年之际,我们与十位与故宫有着各式各样故事的“人”聊了聊,在雕梁画栋、红墙黄瓦之外,描画故宫的另一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32年我只有这一个目标 崔保贤78岁前故宫保卫处副处长 年我从石家庄干校被调到故宫保卫处工作,一天24小时随时需要站岗巡逻,一轮站岗站3歇6(站3小时歇6小时)。那时觉得故宫四方通达金碧辉煌的,不累,新鲜,然后一站就是32年。 保卫处的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我刚来的时候咱们保卫班只有十多个人,中间扩展到二十六个人,04年我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两百来人了,监控器、警报器、安检措施也早就更新了好几代。但历代我们的目标都是同一个:防火防盗防破坏,总之不能让故宫出现一点损伤。 所以站岗这事儿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不会有多大变化,你要觉得枯燥那还是因为不够热爱。只有当人真的喜欢这份工作的时候,才能坚持这么多年,才能一直保持足够的责任心去留心每一处变化。我在任这三四十年,故宫就起过一次火,失窃过六次——59年、62年、80年有两次、87年、11年,这些刻度都不用特意去记录,全刻在脑子里,忘不掉的。87年8月24日那次起火是因为雷击,有天就有雷,这雷对木质结构的建筑就是天灾。那天我们夜间巡逻的时候发现御花园东边有味儿,还有火光,立马就报告队长和消防队了。得亏发现得及时,景阳宫外头消防队救火,里头我们转移文物、搬抬展柜。从发现苗头到最后扑灭,整个过程只花了3小时。 我这半辈子都在跟故宫打交道,退休之后帮央视做《故宫》纪录片的后勤保障,身边的朋友都是在里头工作时认识的,平时聊天聊的也是故宫那点事儿,已经习惯了。八几年冬天值班的时候得自己烧煤取暖,不像如今站岗都有暖气,现在的年轻人回头看总觉得条件艰苦,但我们当时压根没想那么多,就只想怎么把工作做好。我们的老祖宗风风雨雨六百年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产,我始终觉得自己肩上压着担子呢。 打小在店里长大,故宫四十年来的变化我都熟 王智勇45岁永盛斋小吃店店主 骑河楼大街40号,故宫东城墙外,您进了胡同往右一拐,就是我的店。永盛斋店面不大,进门左右两列摆着八张桌子,客人多的时候,一进门,就能闻到满屋子的肉饼香混杂着大葱香菜的气味,坐在最里面边喝茶边捣鼓手把件的,就是我。您要点餐,先来俩门钉肉饼,配一碗羊杂汤。店里的菜品不多,但这羊肉馅饼,来一口能香到你骨子里。 (来源:大众点评) 别看我这店面小,传到我已经是第七代了。从一百多年前的羊肉床子(注:羊肉铺)到今天,卖生食变成了卖熟食,但食材还是那两样,老话说得好,“回民两把刀,一把牛羊肉,一把卖切糕”。 我自己是75年生人,打小就在店里长大。小时候故宫门票只要一毛钱,也就一盒火柴的价钱。但那时候故宫人少,因为七八十年代,大家生活条件都不好,哪有心思出来逛。这么多年过去,故宫的变化,我们这些小店也能感觉到。比如说游客,几十年前穿深蓝色的工作服,颜色都很素,后来流行港风,来店里的游客都穿着西服、皮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姑娘、小伙子喜欢穿着汉服来逛故宫。 我经常问顾客们一个问题:“你们来故宫是来看什么的?”有人说来看看皇上坐过的椅子、把玩过的玩意儿,有人说来看看皇后戴的珠宝,但我觉得,那些都不是故宫。真正的故宫,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它的一砖一瓦,它背后的建筑技艺,更值得我们好好去看。那么恢弘一个建筑立在那儿,立了六百年,我们就有底气说,我们是中国人。 小店在故宫旁边已经开了一百多年,从公私合营到私房归还,从文革到计划经济,和故宫一样也经历了不少变迁。传到我手里,不敢说发扬光大,但祖宗的买卖,还是要好好守着。不管是饮食还是建筑、历史,其实都是这么一种传承。故宫到今年已经是六百年,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也希望能保护好、传下去。 我与故宫的缘分,始于刚出生的那年 刘顺儿妞90后摄影师 我对故宫的喜欢是循序渐进的。第一次去故宫是在年,沿着中轴线看了个热闹,从神武门走出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留恋。八年后的某天,我在微博上偶然看到一张故宫杏树的照片,红色的宫墙映衬着纯白成簇的杏花,花与建筑呼应的样子特别美。因为这张照片,我激动得第二天就跑去故宫看这树杏花,那时花已经谢了,但我拍故宫的想法已经渐渐成形。 年的春天,我整个花期的每一天都在故宫,拍出了一组花与宫殿的“春日宴”。早上八点半我就蹲在门口等着,故宫一开门就冲进去。我的拍摄节奏是根据花期来,先拍海棠,后拍梨花,再拍丁香。早上人少,就先去拍大场景,下午拍人少一点的角落,每天都根据不同的花期和人数情况去拍摄,做了特别细致的排布。这一年,我拍了很多很多的海棠,从海棠刚开花到花落的整个花期,我基本上都在。我才发现原来海棠刚开出花的时候是淡粉色的,而且几乎没有叶子,都是很嫩的小芽,远看是梦幻般大片大片的粉色,装点出一个超乎寻常想象的“粉色故宫”。随着花儿慢慢开放,海棠的粉色逐渐褪成粉加白,再变成几乎全白。 (受访者供图) 拍故宫之前,我已经在京都拍了两年红枫与寺院。浓烈热情的红枫跟幽静的寺院放在一起,有很特别的反差之美,那时候我就已经着迷于花木与建筑的呼应。对我来说,建筑是庄严肃穆的存在,花儿又是充满活力的,如果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花儿的生命力让那些建筑变得不再有距离感。 要知道故宫的美是需要被发现和再创作的。我不想局限于许多摄影师偏爱的广角镜头下恢弘庄严的宫殿,更想去寻找故宫柔美的细节或者精致的角落,多元的身份视角就是发现故宫之美的一把钥匙。你如果守过、看过故宫花树的春夏秋冬,就会感叹原来它在不同的时刻,有着这么不一样的美。我自己以前写过一句话:“对于故宫,你越懂她,就越能发现她美在细微之处,精致是她的骨血。”你会发现故宫不是一个遥远的、有距离感的古代皇城,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同时又非常有生命力,永远璀璨如新。无论是拍故宫的雨后倒影,还是故宫的猫、故宫的灵,我都是在捕捉故宫的这种生命力。刚出生的时候,父亲差点给我取名叫刘璃瓦(琉璃瓦),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与故宫的缘分就注定了。 原来这个华丽的宫殿,处处藏着这么多讲究 海清少年游80后历史文化纪录片编导我小时候就来过故宫,当时只记得被人群簇拥着有点像赶集一样,穿过拥挤的一个又一个的高大的建筑。高高低低的台阶都是白色的大理石,抬头望一下,满眼都是黄色琉璃顶、红色墙壁的大房子,感觉就像在云端一样。重重高大的台阶上,大殿前面有一个姿态特别优美的铜鹤,我那时候小,感觉铜鹤像天上的大鸟一样,需要仰望才行。我记得家人抱着我,高高举过头顶,我居然发现了铜鹤的背后有一个盖子。等我下来的时候跟人说,谁也不信。 后来工作进了故宫摄制组,有了一群嘻嘻哈哈的小伙伴,拍摄完了,我们不知天高地厚地约定去太和殿广场踢毽子。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了大殿的台阶上,我又一次发现了那个铜鹤背后的秘密——它后面的盖子原来就是个可以打开的机关。这仿佛一个秘密通道,一下子又让我穿越回童年。我专门去请教了一位研究建筑的老专家,才知道了故宫仙鹤的活盖都可以打开,身体里面放香料,活盖打开后,仙鹤张着嘴就能“喷云吐雾”,让整个大殿都笼罩在香气之中,气氛也就变得神秘而庄严起来。从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华丽的宫殿,处处藏着这么多讲究,真是拜服了。 (来源:微故宫) 故宫除了让我感受到设计的匠心,还让我发现了画面语言的魅力。在故宫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有一个在养心殿拍的镜头,是日本摄影师赤平勉和赵小丁老师共同完成的。导游带着一组游人,从养心殿院落的外面缓缓进入养心殿;院落里,一组大臣觐见皇帝;养心殿里,乾隆皇帝在沉思冥想。这一个镜头变换了三个场景,穿越了两个时空,从今到古,完美演绎了养心殿的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功能,以及今天观众对养心殿的追寻和探秘。我当时作为一个编导助理,实在是觉得开眼。今年是故宫年,但我觉得年,年,年,其实没有什么不同。她永恒的美就矗立在那,而我们短暂的停留,其实就是时间沧海里的一粟。 我对爷爷心心念念的故宫着了迷 南十方30岁设计师 我不是北京人,但从95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去了17次故宫。最开始两次去故宫,是95、96年跟着父母连续去了两次,但当时我才5、6岁,对故宫的印象就停留在——天安门后面还有很多扇门,感觉这无数扇门很好玩。再后来,我总是和爷爷一起看清宫剧,每当出现这些宫殿的时候,爷爷就会怀念起故宫来。 爷爷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年出生。他提起故宫,总是有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在他这个参与过年开国大典群众游行队伍的人眼里看来,故宫是个旧社会帝王居住的地方,是应该去批判的。而另一方面,他对故宫又有着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慨叹与怀念。他上中学那会儿,故宫刚开放不久,那时候进去不知道是免费还是很便宜,去的人特别少。所以每次要考试了呢,他就喜欢跑到故宫里面去复习,求个清净。诺大的皇宫里,他一个少年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坐着看书;学累了,就在宫里四处走走,看看花看看房子,想着几十年前还是怎样的王公贵族居住在这。每当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就背上包慢悠悠地出宫去。 我对爷爷心心念念的故宫着了迷,实在太想去故宫好好看看了。年的暑假,同样喜爱历史的父母答应放我一个中学生独自去北京看看故宫。那天热得快让我中暑,人也多到我差点被挤得在贞度门摔个跟头,广播里也不停播着“来自XX地方的XX,您的家人正在乾清宫等您”。我还是兴致勃勃地独自在故宫泡了整整一天,中午就蹲在故宫吃了碗泡面。逛宫殿的时候,我会想象百年前的人是如何在这里生活,想象自己的爷爷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是怎样在这里学习、游玩。我对故宫的好奇实在是憋了太久太久,怎样都不觉得累。 我毕业后从事了设计行业,还是习惯时不时去看看故宫,观察建筑的精妙设计,比如保和殿后面的云龙石雕、殿顶的藻井等等。故宫见证了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回顾这么多年,故宫对我来说就像一座宝藏,它的魅力从来不曾随着时间而褪色,反倒是不断增强,每次去北京的时候拜访故宫,在我心中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百年前这里也是许多人真实生活过的地方 兮兮30岁汉服体验馆店主 我们木兮有枝汉服店开在张自忠东四十条胡同里,这里是很纯正的老北京胡同,离故宫、国子监这些博物馆和古建筑很近。半数以上的客人都是去游故宫的,他们几乎都是90后和00后,考古学博士、做开颅手术的手术室护士、高铁乘务员、餐厅服务员……各行各业的人我们都遇到过。 今年9月的时候遇到了两个刚上大学的小姑娘,她们很想穿着汉服游故宫年大展,但是家里人不支持穿汉服出行,就偷偷了买了两身明制汉服借店里的试衣间更衣。她们第一次穿汉服出门,担心会收到异样的眼光,但看到故宫里有不少人也穿着汉服就没那么忐忑了,还跟我们约好下次一同出游。 去年冬天有两个广西的女孩也是特意来借汉服去故宫玩,其中一个女孩的男朋友在部队当兵,等她晚上回来的时候部队已经马上要熄灯就寝了,她男朋友着急地打视频电话来想再看看她穿汉服的样子,当即在店里煲起了睡前电话粥。我们的第一位客人小蟹,当初是被故宫吸引才来到了店里,现在是我们的义工簪娘。冥冥之中似乎是故宫在帮我们与这些同好结缘,因为他们的鼓励和约定,我们才有信心经营下去。 故宫以明清时期的大型宫殿为主,而不是园林建筑或者庭院楼台。所以游故宫的客人也会有意识地选择朝代契合的明制汉服,明制汉服相对唐或魏晋时期形制上感觉会更端庄,常见规整、对称的元素。但其实比起宏大的殿堂,相对日常的景观会更吸引我们,因为故宫不仅是几百年来的皇家权力中枢,也是百年前许多人真实生活过的地方,想到他们也曾这样透过窗棂期待着什么,也曾倚靠过这白玉阑干遥望景山,便会有种时空重叠的恍惚感。我想许多客人喜欢穿汉服游览古迹,大概也是想要体验这种融入历史的感觉。 (来源: 木兮有枝汉服)我重复的第无数遍,可能是观众的唯一 张潇文23岁故宫志愿讲解员 说来惭愧,在成为志愿讲解员之前,我甚至没有去过故宫。大二下学期,一个很偶然的机遇,我参与了故宫讲解员的志愿者招募。没想到的是,我的简历真的在几千份里被选中,还通过了笔面试和两轮试讲的考核,成了珍宝馆的讲解员。去拿出入证的那天,下午刚好有近现代历史纲要的期末考。地铁换乘公交直到神武门外集合排队,一路上我都在拿着复习资料不停地背。拿完证后一路狂奔,才匆匆赶上考试。 这种匆忙的感觉贯穿了我之后两年的志愿生活。故宫志愿者每周定时定岗,学生时代,我只能找没课的半天去做讲解。大三时,要求周三下午1:30必须到岗,而我上午11:30才下课。所以即便老师不拖堂,我也只有两个小时奔到岗位上。那一年的周三,我中午几乎没吃过饭,往往是随便掰一根香蕉,背着电脑就往地铁站跑,不停地跑,然后赶紧上车。 我很享受做讲解时观众被我吸引过来的感觉。故宫提供的学术资料有68页,讲解员对每个细节都要能信手拈来,对于几乎是历史小白的我,啃资料要花很大功夫。但讲解时如果遇到感兴趣的观众,是真能看见他眼睛里有光,这就让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我们总是称呼参观者为观众,而不是游客,这是对参观者的一种尊重——这些“观众”看文物、看宫殿,把这年的历史尽收眼底。 大前年的一次志愿讲解,有个小姐姐全程认真跟我走完了珍宝馆。很巧的是,她跟我同龄,从广东来北京参加保研考试,我们加了
|
当前位置: 个旧市 >故宫六百年,10个人的10段故事特别
时间:2022/12/1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故事我在社交软件上,和古代皇帝谈了许久的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